百事通!“漂来的北京城”与“东方科学之光”
735年前,1291年1月26日,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开凿修建通惠河。
两年后,工程竣工,《元史·列传·卷五十一》记载:“帝还自上都,过积水潭,见舳舻敝水,大悦,名曰通惠河。”沿用至今的名字,自此而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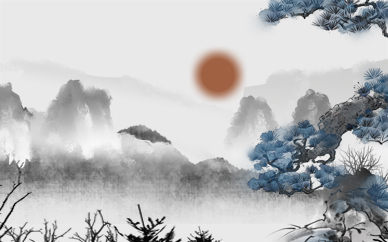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如今的积水潭北岸高地上,矗立着一座原址复建的汇通祠,纪念的正是这一杰出工程的缔造者——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。
今天,重温郭守敬的故事,相信会刷新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认知。
(一)
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言,“与历史上的北京城息息相关者,首推白浮泉。”白浮泉,正是郭守敬为开凿通惠河所寻水源。
元代定都后,北京经济与人口迅速发展,粮饷供给等物资严重依赖江南漕运。可从通州到大都的最后20多公里,车载人扛,极费人力畜力。
打通这最后20公里,难度不小。通州与大都之间,没有适宜的天然河道,且大都地势高,运河的开凿,必须解决在大都附近找水,以及调节水势的问题。
彼时,玉泉山水系虽为现成水源,但水量不足且需供皇宫使用;而永定河水流湍急,也无奈放弃。年过六旬的郭守敬,踏遍京郊山水,历尽千辛万苦,终于发现昌平龙山东北麓的、属于温榆河水系的白浮泉。
水源确定后,郭守敬结合多年经验制定了一份水利图,大致可分三段:以白浮泉为起点,引水向西流,沿着西山山麓向西南再转向东南,流入瓮山泊(今颐和园昆明湖)。如此绕道而行,为的是汇聚诸泉、增加水量,同时建设堤坝工程,解决引水与防洪的矛盾。据考证,白浮引水行经的路线与现在京密引水渠基本吻合,足可看出郭守敬地形勘测技术之高超。
其下再通过长河,引水入大都积水潭,并将此作为泊船终点码头。当时的积水潭(即为今天什刹海的雏形)“汪洋如海”,又称“海子”,在蒙古语中即花园之意。尤其是盛夏之际,清荷暗香,商船云集。
积水潭以下,则重新开挖、疏浚了金朝“旧运粮河”,使引水沿之经通州东南至高丽庄入白河。在这段主要航道上,巧妙设置了坝闸与斗门,以起到稳定通行、“过舟止水”的作用。
通惠盈盈、畅通南北,“京师无转饷之劳”,大大便利了物资交流,促进了元大都的繁荣发展。此后随着朝代更迭,通惠河航线长度有变,但其运输功能相当重要,直至清末京津铁路竣工,漕运才逐渐式微。故而谈起北京的营建史,不少历史学家皆称“漂来的北京城”。
(二)
如今,每每行走在郭守敬纪念馆、八里桥、庆丰闸等遗迹,或是乘坐已旅游通航河段的游船,无不让人怀想旧时光里的摇曳水声,亦感叹古人智慧之不朽。
可若论郭守敬最伟大的成就,并非耀眼的治水功绩,而在于主持制定中国古代最精密,也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《授时历》。
面对当时计时体系严重失准的难题,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编制新历时。郭守敬使用实测方法,主持了一场全国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“四海测验”:在全国设立27个天文观测站,派遣监候官14人分道而出,自己也跋涉千里,观测范围“东至高丽、西极滇池、南逾朱崖、北尽铁勒”,以采集日月星辰的运动数据,观察规律、“敬授民时”。由此测得的回归年长度为365.2425天,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仅相差26秒,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,比同时代欧洲领先近300年。
“历之本在于测验,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”。面对原有仪器年久修失、精度失调的情况,郭守敬在三年内就研制出简仪、仰仪、玲珑仪等十多种新仪器。尤其是,他将结构繁复的唐宋浑仪进行简化设计,使得测量天体位置更加实用、精确、简单,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。
历法编纂的精度,同样见证着郭守敬深厚的数学功底,比如弧矢割圆法、百进位制等的创造性应用,在13世纪皆极为罕见。同时,他还建立起一整套从观测、计算到制定、推广的科学工作制度,堪称“科研团队模式”的雏形。
“他重新定义了中国古代的时间,也打通了北京城的命脉”。从星辰到河渠,郭守敬所取得的成就彪炳史册。郭守敬被李约瑟称为“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”,也被当代科技迷赞叹为“穿越者”。为致敬这道“东方科学之光”,国内外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小行星、月球环形山及天文望远镜。
(三)
翻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,像郭守敬这样卓越的科学家或工程师不少。比如,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,发明地动仪的张衡,编纂《梦溪笔谈》的沈括,著有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……尽管他们在当时的第一身份多是官员,可于后世而言,其流芳首先是因为在水利、地质、工程、天文、药学等方面的专业成就。
中国古人以“格物致知”的方式,“经世致用”的态度,以及“保守述成”的记录传承,孕育出让人惊叹的发明创造。在东方古代的实践之中,科学也好,技术也好,从来不只是复杂冰冷的成果,而都直接服务于生产生活。所谓仰望星空、精研天道,最终皆是为了脚踏实地、造福百姓。
可这样的实用模式总伴随着一个争论: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?持截然对立观点的两派中,都有颇具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。
称“无”者,如爱因斯坦认为,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有“两个伟大的成就”:一是“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”,二是“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联系”;而“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”。
称“有”者,代表人物是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巨著的作者李约瑟,他认为,尽管“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”存在弱点,但是,“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”,而且“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,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”。
可以看出,称“无”者,所使用的大抵是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标准;称“有”者,则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理解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科学以及标准。试图厘清这段争论,需要回归到科学的本来定义上。
“科学”源于拉丁文Scientia,意为“学问”“知识”,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,其含义本身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。以发展的视角来看,科学理当是自古至今延续发展的传统,其中可以有技术传统、哲学传统、实验传统。
尽管如今一提到科学,许多人的反应皆是西方现代科学,但究其根本,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指导实践的工具,是不断完善的认知体系。以此广阔多元的视角来看,中国古代当然是有科学的。否则,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程度,皆远超欧洲、领先世界,又将如何解释?
(四)
这些年,越来越多人发现,无论是科学中心主义视角、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还是中国传统哲学视角,都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。如果打破上述种种,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实践,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视域之下,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价值与意义。
以多元而非狭隘的视角来看,我们能从《墨经》中看到实验思维,从《本草纲目》中看到分类思维,从《天工开物》中看到技术集成……更不用说,那些深度融入古代经济社会,从而带来社会繁荣、甚至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技术。长于经验与实用的技术传统,同样需要建立在观察探索、实践检验的基础之上,其独特应用价值也应该被珍视和认可。
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,不管是科学、还是技术,都从来不曾缺位。某种程度上,也正因有绵长辉煌的技术传统,有漫长经验的积累与沉淀,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,能够在如今的科技创新赛道上,很快实现追赶与跨越。
今天,当人们在什刹海畔瞻仰郭守敬铜像时,仿佛能看到科学之光穿越时空,照亮中华文明对未知的持久求索。当从灿烂文明中走出来的东方国度,愈加自信地拥抱现代科学,一定会以更加昂扬自信的风貌,奔赴下一程星辰大海。
标签: 最新资讯

















